- 热搜词
88pt88大奖游戏888:腊月二十三:老北京祭灶供品有点“甜”~
老北京忙过年的事儿,从腊八开始,到腊月中旬忙碌,而腊月二十三以祭灶为标志,称之为“过小年”,正所谓“糖瓜祭灶,新年来到”,正式进入送旧迎新的阶段了。
小时候盼着过年,是为了能放烟花爆竹、敞开肚子吃好吃的;上学时盼着过年,是为了能有几天不学功课也不会有人在耳边唠叨的日子;而现在盼着过年,细想想也许纯粹是为了能在《春节序曲》那欢快并悠扬的乐曲声中寻找往昔美好而幸福的回忆……
岁月无声无息地流逝,除了回忆,也许并没有留下什么真正的痕迹。而回忆本身也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就拿“过年”二字来说吧,父母那一代人关于过年的习俗,跟我们这一代人迥然有别,而我们的下一代人听我们讲儿时过年的习俗又像听天书似的,总觉得繁琐而无聊,在无形中,很多传统就这样不存了。祭灶,就是其中之一。
时间:二十三还是二十四?
北京俗曲《门神灶》中唱道:“年年有个家家忙,二十三日祭灶王,当中摆上一桌供,两边配上两碟糖,黑土干草一碗水,炉内焚上一炷香,当家的过来忙祝赞,赞祝那灶王爷降了吉祥。”虽然通俗,却也简明扼要地把祭灶的大小事宜说了个清楚明白。
祭灶这件事儿,据民俗学家金受申先生考据,在宋代是在腊月二十四日。“范石湖《腊月村田乐府引》上说:‘腊月二十四日夜祀灶。’《梦华录》上说:‘十二月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现在用二十三日的缘故,也许是应在后夜祭,便算二十四日上午,真实缘故是没法证明的了。”而笔者在明人陆启浤的《北京岁华记》中亦找到“二十四日祀灶”的记载。有趣的是,笔者的妻子是南方人,我们第一次一起过小年时,她很惊讶,说北京怎么会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啊,我才知道南方的“小年”多还是在二十四日,后来看《日下旧闻考》上说祭灶一事,京师“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户则用二十四日”,不禁感慨这便真是存了古风。
祭灶,顾名思义,是祭祀灶王爷。灶王爷在我国古代仙班里的地位并不算高,大概属于基层官员,但县官不如现管,尤其管的是一家人生存最基本的果腹,这就不敢不供奉了。大部分北京家庭是把灶王爷供奉在厨房的大灶旁边,墙上贴一张从纸店或香蜡铺“请”回来的灶王爷画像,下面钉个三角木架,架起一块小木板当桌子,上面放香炉、蜡扦和供品。“老北平”白铁铮先生在书里说:“在三十年代的北平,有佛堂的人家,当然有供奉灶王爷的所在,穷得只赁一间小房儿,坐于此,厨于此,工作于此,穷得这样儿,可是他们也忘不了在墙角上吊上一块木板儿,在木板上供奉灶王爷。”供奉灶王爷不用花费太多,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图的个虔诚。对穷人而言,他是最接地气又最好伺候的神祇了。
老北京传说,因为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往人间各家各户观察人们行为善恶的神仙,负责把各家各户主人的行为记录下来,于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日回到玉皇大帝那里报到,遂有此祭,以求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其实这是误解。祭灶的原意是在除夕前七日为“小令节”,又称“交年”,举行祭礼,因此可以知道祭灶也是“令节祀”的一种。但在老百姓看来,一切礼法的设定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过日子,所以老北京的俗曲唱起祭灶,还是照着传说的意思来:“腊月二十三,呀呀哟,家家祭灶,送神上天,祭的是人间善恶言……当家人跪倒,手举着香烟,一不求富贵,二不求吃穿,好事儿替我多说,坏事儿替我隐瞒。”
灶糖:关东糖还是南糖?
祭灶所用的物品,皇宫里用的是黄羊,直到清末,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里依然说“近闻内廷尚用之”,但在民间,则首重灶糖,就像《旧都文物略》中所言“其供品则唯一以糖为主,而灶糖则为专用之名词。”
灶糖主要有两种:关东糖和南糖。《京都风俗志》上说:“‘祭灶’以胶牙糯米糖,谓之‘关东糖’;胡麻糖片、胡麻条及糯米细糖、梨糕等糖,总谓之‘南糖’,又糖瓜、糖饼等糖为献,方圆形相,殊多品目。”所谓糖瓜,其实与关东糖是同一种材质。在清代,这种糖大部分是从东北贩运过来的,旧时管东北地区叫关东,遂得名“关东糖”;也有一说是因为每到冬天,来自东北的客商带着关东糖、烟草、松子之类的货物来京销售,大都住在朝阳门外东岳庙东的“关东店”一带,是而得名。至于南糖,多以小巧玲珑见称,有冰糖花生仁做成的“花生酥”、外蘸芝麻的“芝麻鸡骨”、内灌酥糖末的“带馅鸡骨”,还有外面芝麻中间加澄沙的“澄沙圆”,但总的来说,在祭灶时的“上桌率”都远不如关东糖。
关东糖是用麦芽和黄米(或糯米)一起上锅熬成浆,逐渐加热浓缩制成的。熬好从锅里盛出,倒在撒满面粉的石板上冷却,之后通过揉搓使它变成不同的形状,如果是棍状的就叫关东糖,如果是瓜状的就是糖瓜了。糖瓜分有芝麻的和没芝麻的两种,最初坚硬无比,摔都摔不碎,想吃得用刀剁,后来经过改革,中间形成蜂窝,所以口感酥脆,加之色泽白皙,旧京走街串巷的小贩叫卖关东糖时往往吆喝“赛白玉的关东糖”。老北京俗话说:“送信儿的腊八粥,要命的关东糖,救命的煮饽饽”,意思是一喝腊八粥就快过年了,一到吃关东糖,年关债主就该上门逼债来了,一到吃煮饽饽(这里指的是饺子),就是除夕吃饺子,债主一般不会再来,这一年的债就算是躲过去了。
笔者幼时,一到冬天,甭管是卖冰糖葫芦的还是卖报刊杂志的,但凡是个摊点,一进腊月就开始有关东糖卖。因为天气冷,关东糖虽然凝固得很坚实,但里面又有些微小的气泡,所以吃起来别有一种脆甜香酥的感觉,此外,因为原料是粮食,是以入口有一种特殊的香气,为其他糖果所绝无。只是此物实在粘牙,难怪在晋代《荆楚岁时记》里取名叫“胶牙饧”,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岁盏后推兰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咏的亦是此物。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后来的麦芽糖不知是原料的问题,还是制作工艺的问题,不但没有了一点儿麦香,而且比以前更加难嚼且齁甜齁甜的,我也就不再买来吃了。
供品:一碗凉水献给灶王爷?
1916年出版的《北京指南》一书中写道:“二十三日祭灶,供以糖饼、糖瓜、黍糕等品,又备草料、凉水,谓用以抹灶君之马,祭时必以炉火炽盛,以糖饼置炉口,亦有缘而涂之者。相传灶君朝天,白人家善恶于玉帝,以行赏罚,置糖炉口则口黏不复能语,故焚神纸时,必祝曰:‘好话多说,不好话少说’。祭毕,以糖果与家人食。”从上文不难看出,祭灶之所以要预备灶糖,目的很简单,一方面是请他在玉帝面前多多美言,另一方面是粘上他的嘴让他不能说太多,这看起来很矛盾,其实倒反映出人们真实的生活情态,家长里短、酸甜苦辣,很多事情是没法以简单的好坏标准来评价的,不如吃糖。除了灶糖之外,祭灶时必不可少的祭品还有干草豆料和一碗水,这是给灶王爷骑的马预备的草料——可能有人会说,城市家庭哪儿那么容易找干草豆料啊,不用急,腊月二十三之前,粮食店专门会售卖或赠送这两样东西给主顾。
祭灶的仪式其实很简单,腊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晚饭后,在灶王爷画像前的桌子上摆上供品,焚香礼拜之后,把那张烟熏火燎了整整一年的神像从墙上揭下来,和金银锞、黄表纸等等一起焚化,送灶王爷上天去向玉皇大帝述职了,然后拿些关东碎糖,放在灶口儿上,这就算是粘住灶王爷的嘴了。剩下的关东糖当然是被孩子们分着吃掉了。不过更令孩子们高兴的是,从这一天开始就可以敞开来放鞭炮了,《春明采风志》有云:“刍豆才陈爆竹飞,家家庭院弄辉辉,灶王一望攒眉去,又比昨秋糖更稀。”描述的就是这一景象,从这一天开始,家中就算是没了一家之主(旧时灶王爷画像上都贴有“一家之主”的横批),直到除夕接神时,再把新请来的灶王爷画像贴在墙上,依旧焚香礼拜,才算神归旧位。
在学者刘叶秋先生的书里读到过,那时有钱人家祭灶时的供品,还真不是普通人家所能比的。“要在院内立起‘天地桌’来,把一张大方桌放在正房的廊檐下,陈设香炉、蜡扦,用木头牌位或长方形红纸,写上‘天地神祇之位’,供在中央”。而供品多为干果,如荔枝干、桂圆干、花生、栗子、红枣等等,给灶王爷嘴上涂蜜的东西也是有的,可不是关东糖,而是从著名的糕点铺正明斋定制的蜜供——一种蜜制的面食,以许多小长条架空连接,色作金黄,顶尖下方,高矗如塔。不过蜜供不宜放在院子里陈列,怕风过沾土,祭灶后就拿回屋里,而干果则从腊月二十三一直摆到正月十五。
有富贵的,就有贫穷的,有些实在穷得不行的人家,连关东糖都买不起,但祭灶仪式不可少,就直接供奉一碗凉水,嘴里面还要念念有词:“灶王爷,本姓张,一碗凉水三炷香,今年小子混得穷,明年再吃关东糖。”
哪怕穷得揭不开锅,腊月二十三都要祭灶,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大约都是愚昧迷信作祟。笔者却不这么认为,有些传统里固然有一些迷信的成分,但总的来说,老百姓求的就是一个心安,求的就是过年过得更有气氛而已。说真的,又有几个人真相信世界上有灶王爷爷和灶王奶奶呢,那些吃着关东糖的小脑瓜子里早已把他们想象成自己爷爷奶奶的模样了吧。
-
 足球单场专家推荐:国防部:遏制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02-05
足球单场专家推荐:国防部:遏制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02-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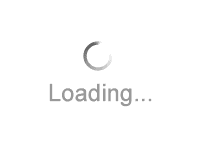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郭文海:让敢负责、勇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有舞台02-02
郭文海:让敢负责、勇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有舞台02-0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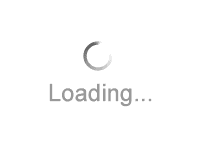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bet9备用登入口:柳传志惊涛骇浪35年 打造“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02-05
bet9备用登入口:柳传志惊涛骇浪35年 打造“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02-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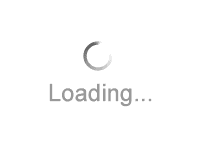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万博官方manbetx网页版:《天地劫幽城再临》幻海迷城攻略 幻海迷02-04
万博官方manbetx网页版:《天地劫幽城再临》幻海迷城攻略 幻海迷02-0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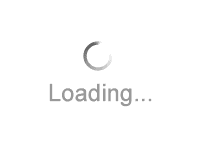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贵州桐梓到渝发布精品旅游线路02-02
贵州桐梓到渝发布精品旅游线路02-0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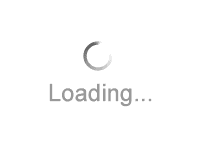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万鑫娱乐:汤加附近海域发生5.1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02-03
万鑫娱乐:汤加附近海域发生5.1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02-0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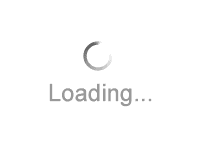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博体育官网:宁德公安局:全面推进安全生产 筑牢群众安全屏障02-05
博体育官网:宁德公安局:全面推进安全生产 筑牢群众安全屏障02-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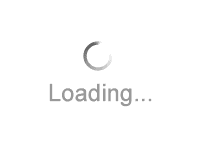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w88优德金殿手机版:重庆新开554路公交线 商务学院至文旅城的乘02-04
w88优德金殿手机版:重庆新开554路公交线 商务学院至文旅城的乘02-0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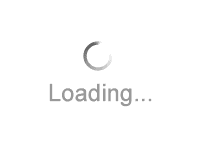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金沙赌玚登录:英超综合:曼城稳健得胜 利物浦再“掉链子”02-05
金沙赌玚登录:英超综合:曼城稳健得胜 利物浦再“掉链子”02-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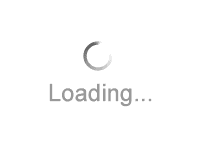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澳门24小时线路检测:特朗普前竞选律师涉嫌欺诈被调查:选民资02-03
澳门24小时线路检测:特朗普前竞选律师涉嫌欺诈被调查:选民资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