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搜词
发条娱乐棋牌官网:给井干爷拜年~
寒假回老家,虽然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可我还是没有忘记去看一看我儿时认下的井干爷,并给它拜了个早年。
井干爷就是故乡淮花湾前面的老井。三十多年前的一天,听说父亲要我认老井做干爷,我哭喊着不愿意。可小小的我怎能拗得过父亲,他一只手就将我提到井口旁边,脚往我的腿弯儿轻轻一点,我便跪了下来。妈妈在一只大海碗里摆好了芋头、干枣、窝窝坨,又在盛满高粱的碗里插上三根燃着的香,随后“噼里啪啦”放响一挂小鞭。我便在小伙伴们“嘻嘻哈哈”的笑声里,泪眼婆娑地给老井磕了三个响头,用哭腔叫了一声“干爷”,才算了事。
井干爷的井口是用八块青石压砌而成,呈四平八稳的“井”字结构。井干爷的井口是方的,井身却是圆的,是用弧形青砖旋砌而成。砖的上面爬满了毛茸茸的青苔。井口三尺见方,可容两只木桶同时打水。对着井口望下去,黑黝黝的,好像一个人会说话的眼睛。说也奇怪,井干爷一年四季水位不变,水面到井口始终保持着一丈的距离,旱季亦然,这让好多人大惑不解。
村里的私塾先生说,井外方内圆,暗合天象,这和古钱币的造型相似,圆代表着天,方代表着地,其间包容着怀阴抱阳的意象,蕴含着执阳含阴的易理,老井井脉造化自然而随心,顺应万象而不变,乃尔等福祉也!我虽然听不懂私塾先生文绉绉的话,但从旁听者啧啧赞叹的神情中,我知道先生是在夸奖我的井干爷。于是,我原先对井干爷的不满也便慢慢释怀,开始从心里喜欢上它了。
井干爷水质清冽,冬喝不冰牙,夏饮不伤胃。冬天,白雪拥着井台,而井口却热气腾腾,如同我嘴里哈出的热气。“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这首流传下来的打油诗该是对冬天井干爷的生动写照。夏季,我喜欢坐在井干爷旁边的柳荫下乘凉。此时,井干爷悄悄地向我吐着阵阵凉气,它身后的深水塘里荷花正开,清香袅袅拂来,我不由腋下生风,神清气爽。
井干爷的水烧开之后从来没有白色的水垢,修吊子底和钢筋锅底的人从不光顾淮花湾。那些吊子用了十余年,依然崭新如初。公社几个嗜茶干部泡茶,也喜欢骑着车跑到淮花湾打井水。他们说,用我井干爷的水泡出的茶,汤色清澈,茶儿绵软,余味悠长,茶味要比公社院子里的水井水不知要好多少倍。
井干爷水质如此受人青睐,自然也让人做多种猜测。有人说井干爷的井脉直通淮河,有人说井干爷和身后的深水塘同宗,属地下同一眼泉水生养而成。村里私塾先生却说,井干爷养育着一条井龙,井龙在地下钻道可以直达东海。我们做孩子的听私塾先生说得神乎其神,便万般想象着井龙的模样。扁头说井龙像泥鳅,二蛋说井龙像黑鱼,丫头说井龙像长蛇……我却想象着井龙应该像大树的根,想扎到哪儿就扎到哪儿。
为了验证各自的说法,我们常揭开井干爷的木板井盖儿,围爬在井口旁,睁着眼睛看井龙出现。可是,我们除了看到水井里一张张好奇的嫩脸之外,剩下的就是在井底晃荡不已的脸盆大小的天空。看不到井龙,我们便去找村里的井把式老罗锅,因为全村只有他下到过抽干的井底。他可以作证井干爷到底有没有井龙,井龙又到底是何模样。我们几个孩子排除万难,才从生产队瓜地里偷来了三个大西瓜,咽着口水贿赂了老罗锅,老罗锅这才愿意向我们讲述他下到井底的所见所闻。
和所有询问过他的人的答案一样,老罗锅说,他下到井底淘井,只看到两眼小儿手臂粗的泉水旺旺地向上喷涌着浪花,根本就没看见井龙的影子。他见我们有些失望,马上又说:“井龙属神物,我一介凡人,怎配看见?况且井龙见水快要被抽干,还不早就顺着泉眼钻回去躲起来?!”对于老罗锅的回答,私塾先生却微笑不语。他说,老罗锅一定看见了井龙,他之所以不敢说出来,是怕泄露了天机遭到天谴。虽然得不到肯定的答复,但我们却都相信井龙一定存在,而且坚信它也一定会用水托住失足落井的孩子,让他像是在陆地坐板凳一样,平安无事。
大年初一,井干爷也和所有人一样,要整整休息一天,美其名曰:“歇井”。所以,挑水时间最迟到年三十的晚上。大年初一一天,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再揭开井盖,这是祖上流传下来的规矩。这一天的早晨,我也会跟着妈妈,早早地去给井干爷拜年。
如今,我的井干爷涌水已经不像当年那么旺了,村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很少有人去挑它的水吃了。有人担心小孩子会掉进井里,提议把它填平。母亲听说了,坚决不同意,她老人家自己出钱请木匠做了井盖子,这才保住了老井。
一直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父母为什么认老井来做我的干爷。老井不像河水,四处流浪,居无定所。老井像庄稼一样,它是有根的。它的根深深地扎在大地的心窝上,牢固而安稳,敦厚而善良。有了这样的干爷庇佑我,我自然就会平安长大的。
小年的早晨,我带着孩子,在老井边摆上了水果,燃上了三炷香,恭敬地给老井磕了三个响头,并大声喊了一声:“井干爷!干儿子给你拜年了!”我的孩子听了,一阵嬉笑,可我却流出了眼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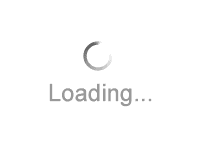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宝盈bbinAPP下载:新春走基层|民警夫妻:节日“偶遇”02-15
宝盈bbinAPP下载:新春走基层|民警夫妻:节日“偶遇”02-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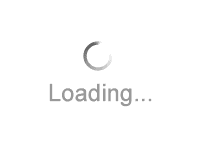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十三五”成就巡礼】优先发展教育 办人民满01-28
【“十三五”成就巡礼】优先发展教育 办人民满01-2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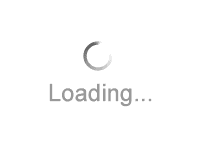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永乐国际直选乐在其中:打麻将连输3万余元,长沙女子气到报警02-06
永乐国际直选乐在其中:打麻将连输3万余元,长沙女子气到报警02-0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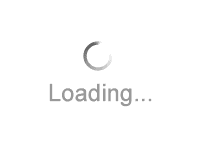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澳门24小时官网:近70家公司发布退市风险提示 专家:尾部公司正02-06
澳门24小时官网:近70家公司发布退市风险提示 专家:尾部公司正02-0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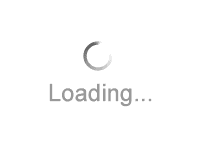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合乐888登录注册:别人家的孩子!天才少年曹原再发Nature,太牛了02-06
合乐888登录注册:别人家的孩子!天才少年曹原再发Nature,太牛了02-0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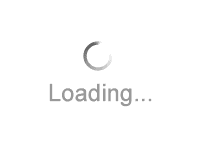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凯发k81111:俄外长:欧盟是导致俄欧关系不和的原因~02-15
凯发k81111:俄外长:欧盟是导致俄欧关系不和的原因~02-15 -
 黄金城网址667722:“90后”民警的第四个就地过年:守护已成习惯02-12
黄金城网址667722:“90后”民警的第四个就地过年:守护已成习惯02-1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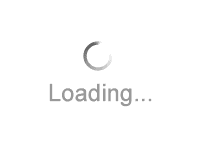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永乐国际AG手机下载:北京今迎雨雪过程 城区能堆雪人吗?~02-14
永乐国际AG手机下载:北京今迎雨雪过程 城区能堆雪人吗?~02-14 -
 新葡萄京官网2018:新春走基层|深夜背着15公斤工具包,“地铁医02-14
新葡萄京官网2018:新春走基层|深夜背着15公斤工具包,“地铁医02-1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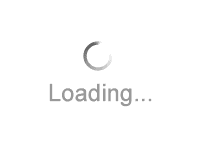 cq9电子游戏:【新春走基层】奋战在地下的坚守者~02-13
cq9电子游戏:【新春走基层】奋战在地下的坚守者~02-13











